夏廷献随笔:海军作家叶楠的遗憾
编者按:2025年是河南信阳籍海军老作家叶楠先生诞辰95周年,清明节到来之际,特发河南南阳籍海军作家夏廷献22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对叶楠先生表示追思和悼念。
夏廷献在文中说到叶楠先生的“第三个遗憾”时写道“如果现代科技能通过什么仪器够接通先生的艺术神经,高速度地传输出文字,这部书很快就可以出版了。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这种科技手段……”
22年前夏廷献的想法就要实现了(已经有“脑机接口”发明了),遗憾的是叶楠先生已经走了,他脑子里已经构思成熟的一部反映中国海军百年史的长篇巨著没有来得及输出成文字,读者也永远看不到了。真是遗憾哪!
叶楠 (1930—2003),原名陈佐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中山铺人,先后就读于信阳女师附小、潢川中学、信阳师范,中学期间,经常与孪生弟弟白桦(原名陈佑华,著名作家)在《豫南民报》《中州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194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参加中原野战军桐柏部队任参谋。1949年冬入海军学校机械工程系学习,1954年结业后到潜艇支队任机电业务长、科长, 北海舰队文化部创作组组长,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1959年,叶楠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文学作品《甲午风云》问世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之后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电影文学。
叶楠的遗憾
作者 夏廷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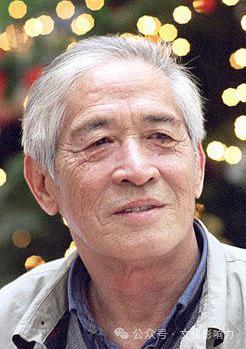
著名作家叶楠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2003年的清明节,著名作家叶楠先生没有突破“73”的劫数,在北京海军总院与世长辞。
叶楠——从河南信阳飘出的一片绿叶,在《甲午风云》《巴山夜雨》中,走完了《绿海天涯》,带着《苍老的蓝》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之中。
笔者把叶楠去世的消息告诉一位文友时,这位文友感叹地说,叶楠先生也算功德圆满了。
是的,世上做人作文如叶先生者,尚不多见,应该说是不枉此生了。
然而客观规律却是:事没有尽善尽美,人总有未竟之事。
我知道,叶先生有三个遗憾。
第一个是,他没有闻到自己在病床上精心选编的“小说集”墨香。这本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领导策划运作的“社版书”——《叶楠中短篇小说自选集》,正式出版前10天,病魔毫不通融地夺去了这位文坛老将的宝贵生命。据说,他在生前曾经看到过书的“校样”,表示了欣慰和对出版社的感谢。但没有看到生平最后一本书的“样书”,也是一件憾事。
第二个是,他觉得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精力分配有些不当。一次他同我聊天时说,我花在影视方面的精力太大,虽然有些收获,但因种种原因,也有不少“无效劳动”,有的甚至是自己花了许多心血的“无效劳动”。如果把这部分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小说就可能写得更多些更好些。2000年9月,他在向我推荐阅读一位青年作家反映中原农民生活的作品《拯救父亲》时,感慨地说,作为河南人,我本应该以自己的眼光和感受,写一些反映乡亲们生存状态的小说,在塑造中国农民“历史形象”上做一些探讨,但我却没有做到,现在想做,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第三个是,身为海军作家,却没有写出一部反映中国海军生活的长篇小说。那一年,俄罗斯“库艇”沉没的事情,对潜艇兵出身的叶楠触动很大。一个阶段,他几乎天天同我说到这件事,感叹中外海军建设中的一些问题。由此引起的话题,说了他酝酿已久的一部反映中国海军百年历史的长篇小说,说了他为此做的大量资料准备和到海军旅顺基地的实地考察。一天晚上散步时,他又进一步向我讲了“故事梗概”——以旅顺口为背景,从俄、日、清、民国海军一直写到共和国的人民海军。我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了他是想来个“最后一搏”,把对大海对海军的爱融汇成篇,献给毕生为之奋斗的海军事业。然而,癌变把他的这一宏愿无情地变成了遗憾。
叶楠的三个遗憾,第一个是一位文友讲给我的。后两个是我不幸因病住院,有幸与叶楠老师为邻,在讨教、聊天中“亲耳”听到的。
三个遗憾,从程度上看,第一个似乎轻一些,因为“小说集”中的11篇作品,多是他的“旧作”,又是他亲自选定的,虽然没有看到“样书”,但内容他是清楚的,只不过没有看到“集合”在一起的“样子”罢了。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所做的工作,使类似我这样的读者在叶楠身后,看到了先生了“自选集”,从而能够睹物思人,见字如面。
先生的第二个遗憾,我感觉比第一个要重。先生是在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回顾后,讲到这个遗憾的。作为一个在影视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获得过“最佳编剧奖”的剧作家,感叹自己在影视领域花的功夫太大,影响了自己的小说创作。这种“反思”,是沉重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先生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并驾齐驱”争相辉映。到了“其言也善”的时候,觉得还是多写些小说为好。这种“肺腑之言”,值得我辈借鉴。
第三个遗憾是第二个的延伸,我感到这是叶先生的最大遗憾。因为当时他曾几次谈到这部书的主题、架构,说到其中的人物。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小人物,是一个理发师。这个理发师由童年到老年,因职业关系——给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海军将领理发而目睹了旅顺口的“海军史”。我当时的感觉是,如果现代科技能通过什么仪器能够接通先生的艺术神经,高速度地传输出文字,这部书很快就可以完成出版。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这种科技手段,病得难以捉笔的先生虽然“成书在胸”,却难以继续“趴格子”留下字迹,只好留下终生遗憾了。作为海军作家,先生写过不少反映海军官兵生活的作品:散文集《海祭》《浪花集》,中短篇小说集《海之屋》《一帆风顺,燕鸥》,电影文学剧本《金锚飘带》等,但从《甲午风云》起就萌发地写一部“百年海军史”的愿望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要是上天再给先生几年时间,相信先生一定会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在先生同我的多次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先生对海军事业的挚爱,感受到了先生想以手中之笔报答大海陶冶之恩的深情。这种“涌泉相报”的精神,是值得我辈铭记在心的。
文学上的未竟事业,别人是很难完成的。文学史上像高鹗那样的高手续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也难免遭人非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叶楠先生的遗憾,是别人无法弥补的,只能是遗憾了。但我辈如果能从先生的遗憾中“悟”出点“什么”,先生也许不会那么遗憾了。
清明节,癸未年的清明节,带着累累硕果,带着对人民海军的爱,带着读者对他的祝福,也带着永远的遗憾,在细雨纷纷的夜色中,叶楠——一片楠叶,轻轻地悄悄地落到了树根。
那一刻,下起了《血红的雪》《花之殇》了,《姐姐》哭了。
那一刻,他书中的人物都来了,《傲蕾·一兰》披着《木棉袈裟》虔诚地为他祈福,《西部歌王》站在《海市蜃楼》上动情地在为他歌唱。
笔者认识叶老30多年,是看着叶老的作品,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由叶老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先生住院时,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病房中的叶楠》在报刊上发表。先生走了这一个多月,一直想写点什么表达一下对先生的追念。想来想去,写下了这篇“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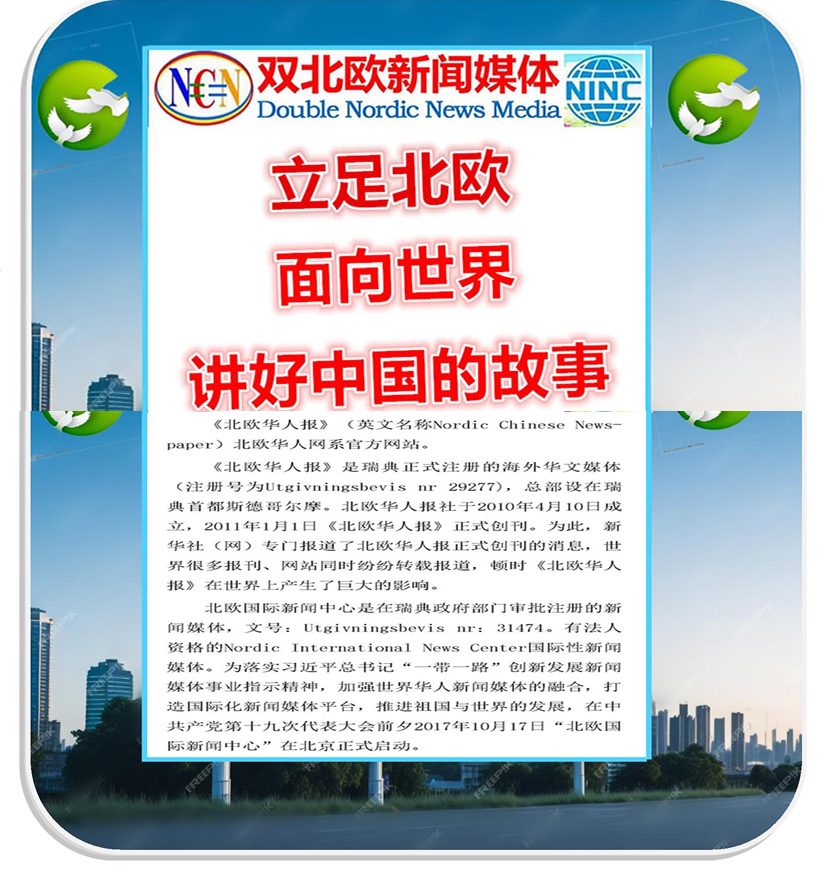

-1-300x15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