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年》
作者 :杨进
提起过年的事,小时候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时,逢着过年,家里的大人是不给孩子压岁钱的,放鞭炮的钱也不给。平日里跟大人要个钢蹦去书摊看本小人书的事倒是有的。
我家兄弟七个还有母亲和一个奶奶,全靠父亲一人工作来养活,日子过的紧巴巴。
不过,过年吃一顿饺子是少不了的,穿新衣服也是高兴的事。记得母亲一边给我们穿新衣服一边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是呵,上过岁数的人谁没穿过带补丁的衣服。
初一早上,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盼着从里面吃出一分或二分的硬币来,寓意着新的一年钱财来的旺,或从里面吃出一块糖,寓意着新的一年生活甜甜蜜蜜。
那年月,日子简单,快乐也简单。
吃完饺子就开始挨家挨户去给邻居们拜年了:一声过年好!李家的婶婶递上两块糖,张家的爷爷抓上一把花生,不大一会的功夫衣兜就满了起来,心里的那个美就甭提了。
院子里有几十户人家,第一个去拜年的是周奶奶。周奶奶是烈属,儿子在青岛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当时正在一条街道上张贴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标语。
上小学时,班里的“学雷锋小组”经常帮周奶奶家打扫卫生,政府颁发的烈士奖状挂在墙上,看见就会想起胸前的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周奶奶是居委会委员,那一天,她到我家来动员我“”上山下乡 ”,还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勉励我一颗红心听党召唤。
周奶奶活了104岁,在几十年前去世,那时,已不讲究拜年了。院子里的人家也大都换成到城里来打工的人家,临到过年时都拎着大包小包的回了老家,院子里冷清了许多。
过年的气氛在院子里消散了,只是我还记得几件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是弟弟看别人家孩子放的鞭炮未响,捡起来放进口袋时却响了,新衣服的口袋被炸出一个烂洞,免不了要挨大人一顿打。二是父亲在灶台炒花生准备年货,锅里掺着小石子,铁铲的搅动发出瘆人的响声伴着焦糊的味道。
“出去玩去”,父亲说。
我仍旧站在那里。
终于,有一粒花生蹦出锅外,小手迅速捡起。
“吃了吧”,父亲说。
后来我去了内蒙支边,快过年时,父亲冒着大雪跑到我两个弟弟“上山下乡”的地方,为我开一份大队,公社和县里的三级证明,我想转插到弟弟那里,离家近些,离亲人近些。
腊月里,放完了牲畜赶回圈栏,我就骑着马去火车站看家里有没有来信。车站那里有一个售票的窗口兼作收发室,连队的信件和包裹都在这里周转。
那天收到家信,信里说我的“药”过两天就寄出 ,其实是“三级证明。当然这是提前与家人约定的暗号。那个年代要求人们扎根边疆,所以怕暴露这事。总之,我和家人扮演过一回“地下工作者”呢。
还记得第一次在连队过年:和留守的几个女战士在一起接生羊羔,初夕夜炉火通红照亮脸庞。人们在一起包饺子,把镰刀把卸下来当擀面杖,在行李箱上擀饺子皮。忘了是谁举着马灯扮演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引来一屋的欢声和笑语。
那年春节接生了三十多只羊羔,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增添一份又一份喜悦。
古人有吟诵新年的诗:“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
如今的年,虽说少了些年味,可是少不了的,依然是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心情。
除夕年来到,万家灯火时。
去年的12月4日传来了“”春节”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遗成功的消息,“中国年”正以华丽的转身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2000年1月29日,为了欢度中华民族传统的新春佳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春节》特种邮票。其中的小型张用农民画的形式表现出北方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团圆欢聚的情景。
过年——正是中国人薪火相传的永恒主题 ,也是中国人亲情与温情的永恒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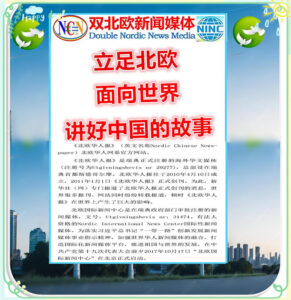

-1-300x156-1.jpg)